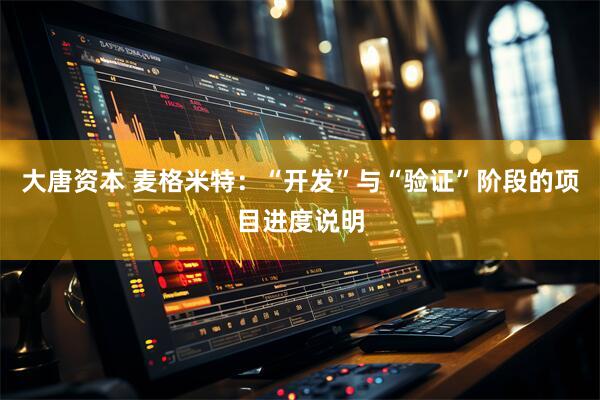电影《我不是药神》上映至今已七年,剧中一群为治疗慢性髓细胞白血病(CML寻牛堂,又称为慢粒)而倾家荡产的患者令人唏嘘。如今,随着创新靶向药物不断涌现,这种曾经的“绝症”已经变成可控的慢性疾病。临床上,医生和患者们奋斗的目标,也从“活下去”变成“活得好”,实现停药和高质量生存。
中年劳动力的“隐形威胁”
慢粒的根源在于骨髓造血干细胞的恶性增殖。“9号和22号染色体发生易位,形成独特的BCR-ABL融合基因,导致细胞失控增长且拒绝凋亡。因此国际慢粒日也定在9月22日。”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刘晓力教授指出,这种基因变异会引发白细胞数量异常攀升。

刘晓力教授 南方+ 严慧芳 拍摄寻牛堂
在中国,慢粒患者中位发病年龄集中在40-50岁,显著低于欧美国家的60-70岁。这意味着主要劳动力群体成为疾病主要影响对象。“许多患者是家庭的经济支柱,疾病对家庭冲击尤为严重。”刘晓力解释。据统计,我国每年新发病例约9300例,但全国性流行病学调查尚未更新。
慢粒起病隐匿,乏力、低热、消瘦、腹胀(脾脏肿大所致)等早期症状常被忽视。“约半数患者是在体检或诊治其他疾病时,意外发现白细胞异常升高而确诊。”刘晓力教授介绍,慢粒的诊断需经过三重验证:血常规初筛、骨髓穿刺观察细胞形态与分期、染色体分析寻找标志性的“费城染色体”以及BCR-ABL融合基因检测。
治疗困境与新希望
靶向药物酪氨酸激酶抑制剂(TKI)的问世彻底改写了患者命运。刘晓力教授回顾:“在TKI应用前寻牛堂,慢粒患者中位生存期仅3年半左右。如今90%以上患者可实现长期生存,CML已成为如高血压般的慢性病。”
但挑战依然存在。约40%患者会遭遇耐药或严重副作用,而且临床研究显示,反复换药的病人预后不良。
现有TKI存在不同局限:一代药易致颜面水肿、肾损伤;二代药常见肝损伤、高血糖、胸腔积液;三代药则可能引发高血压和血栓。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许娜教授指出:“传统药物脱靶效应明显,导致疲劳等不良反应频发。”

许娜教授 南方+ 严慧芳 拍摄
慢粒的治疗目标正在升级——从追求“长期生存”转向“功能性治愈”(安全停药)和“高质量生存”。这一背景下,全新变构抑制剂阿思尼布带来突破。该药物采用独特作用机制:不同于传统TKI靶向ATP结合位点,它精准锁定BCR-ABL蛋白的肉豆蔻酰口袋(STAMP)。“其脱靶效应极低,疗效优于传统TKI,且显著减少副作用。”许娜教授分享了她在临床遇到的一个典型案例,“一名71岁的女性患者,有七年多病史,已经对历代TKI均不耐受,出现严重心血管反应。后来换用阿思尼布后耐受性良好,为类似患者提供了新选择。期待能够尽早纳入医保,让更多的患者用得上。”
随着医保政策优化和创新药物进展,CML治疗正从延长生存向提升生活质量跨越。刘晓力教授特别强调,慢粒是可治可控的慢性病,生存期接近常人,因此规范管理非常重要,病人既要坚定治疗的信心,也不能掉以轻心。“我们曾收治一位32岁女性患者,她在治疗期间意外怀孕,在规范管理下,先后顺利分娩两胎,如今已健康生活近十年。”
南方+记者 严慧芳寻牛堂
银河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